貝茨勛爵徒步日志:Day33 (5月8日): 耶穌會傳教堂避雨記
今日徒步:16.40公裡 / 10.20英裡
累計徒步:827.58公裡 / 514.19英裡
今日籌款:200.00英鎊 + 550.00元
累計籌款:7,545.41英鎊 + 82,549.06元
我確信在個人最終極的價值及在他對於生命的權利上,是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我深信提供有益的服務,是項再平凡不過的人民責任了,隻有在淨化熱情的奉獻中,才能濾除自私的殘渣,也釋放了人性中高尚的靈魂。
我深信在全智及全愛的上帝,不論他是叫什麼名字,並且深信個人最崇高的實踐、最美滿的幸福及最廣泛的效用都將在與其意志契合的生活中尋得。
我深信不疑愛是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它能讓厭惡撫平﹔公理也是,而且能戰勝威權。
—— 小約翰羅克費洛
又是一個暴雨天。而路線的很大一部分就直接暴露在天穹下,電閃雷鳴之間肯定不適合四處游逛。我們到處尋找附近能躲雨的地方,於是就在亞培域(Yapeyu)碰到了一座叫伊斯坦思亞(Estancia)的牧場,這裡原來是一座耶穌會傳教堂。幸虧雪琳發現了這麼好的地方,我們一到牧場就受到了牧場主人Juan和Karina以及他們家火爐的熱烈歡迎。不過火爐一會兒就被我圍滿了濕透的衣服。
一走進這座原來的傳教堂,歷史就仿佛從它的一磚一瓦中滲出來。可惜我從來沒有研究過耶穌會及其歷史對於南美洲的影響。我對耶穌會的印象僅限於我看過的一部特別喜歡的電影——“傳道者(1986)”。電影講述了一個耶穌會傳教士千裡迢迢旅行到此處以北的地方並且試圖向當地居民傳道的故事。
實話實說,我一直覺得耶穌會的傳教士們看起來有點太過認真和自我了。原教旨主義者的樂趣都哪去了呢?人其實不需要多少鼓勵就很容易自我膨脹並且自認為高人一等,所以用道德審判他人和以權欺凌他人就自然而然了。這種情況在當傳教士們認為他們的權利來自上帝親自授予后就更加嚴重。而實際上,我卻認為權利來自於另一個些許不同的角度——同樣有趣的神學辯論發生在大約1550年的西班牙,被稱為巴利亞多利德辯論。
我並不想在這裡對巴利亞多利德辯論進行總結,我也沒有關於這場辯論的充足知識。但它的核心討論點是南美洲的那些野蠻部落居民是應當被以神的名義毀滅,還是應當同等的被主所擁抱。耶穌會教徒們認為他們應當是平等的,因此有權利學習真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歷史上定居在巴拉圭、阿根廷北部和巴西的這部分部落居民是瓜拉尼人,他們有一套自己的創世主信仰。在他們的信仰裡,死后會有來生,而人類終其一生的努力在於創造一個沒有邪惡的世界﹔如果有惡行的出現,就應當向神靈獻祭以取悅神靈﹔在部落裡,進行祭祀活動的精神領袖享有最高的地位。
瓜拉尼人當年認為,借助西班牙殖民者的力量可以保護自己的部落,而他們的宗教和祭司與基督教和牧師也大致相容,所以何樂而不為呢?耶穌會傳教士們在傳教過程中向當地部落提供了教育和經濟活動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保護部落居民不會被奴隸獵手們捕獲。這的確是歷史中不可思議的一章,至今仍很難理解。Estancion, Yapeyu這些地方直到現在依然是研究過去寄托歷史的樞紐。
以我們目前的文明水平、道德水准來評判古人和沒有足夠幸運與我們同步發展的文明似乎已經成為當今,特別是西方文明的通病。我們甚至可以環顧當今世界,看其他地方人們的行為和舉止,然后懷疑,這些難道真的是人類麼?這很像1550年左右發生在西班牙的巴利亞多利德辯論,結論當然是他們都是完完全全的人類並且珍重平等如我輩。對於文明的差異,有一種辦法就是用耶穌會傳教士那樣的角色來教化他們,但這樣就會引出我們自認為比別人優越的討論﹔另一種辦法就是從承認即使是我們自己的文明,也遠非完美無缺。西方文明也曾經為歷史上的累累惡行而愧疚(如種族屠殺)。在謙卑和人性這兩點上,我們可以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這聽起來有點像“道德潔癖”,但我認為在這一點上必須要有一條涇渭分明的邊界,這條邊界能夠抵擋住所有其他企圖越界的借口。那就是所有人類不分性別,種族,年齡,宗教信仰,貧富,性取向,身體狀況或教育狀況,都應當同樣被珍視和被尊重。我們首先都是人類,所有沒有人比其他人更優越,所有生命都應當是珍貴的。這條界線應當是我們進行交流、提攜文明的起點,如果我們認同這條邊界,一切事情都有可能,而一切分歧都可以化解。
 |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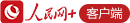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