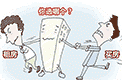昨天的博写到即将动身前往科尔科瓦多山顶的救世基督像。我们选择了穿过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的路线。有四个护林员志愿者与我们同行,个个都身强体壮。登山开始前,护林员会要求游客签字,说明同行的有几人。我起初写下了“14”,但到达山顶时只剩下7位坚毅的伙伴。
自从4个月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动身起,我就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段徒步的情景。这段徒步令我魂牵梦绕,是支撑我战胜各种困难的力量之源。我会躺在床上,想象着登顶科尔科瓦多山最后 3 公里的徒步会是何等情景。仅用“标志性的”来形容里约的救世基督像是不公平的,它一定是世界上仅次于自由女神像最著名的雕像。
基督像始建于1920年,高30米,伫立在海拔700米的科尔科瓦多山顶,俯视着里约热内卢。我的朋友和向导佩德罗 · 梅内塞斯讲述了关于上山小径的一些事:早在雕像造好之前,上山小径就游人如织,因其俯瞰欣赏里约海湾的视角超然独绝。一些著名的英国人,如库克船长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等,都曾踏足此处。小径磨损得很厉害,由志愿者维护,我们上山时还看到他们正在工作。
小径旁高树丛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华盖,遮蔽了山顶和基督像,这也使上山的体验变得无比美妙。树盖也吸引大量的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和猴子。此次徒步99%走的都是柏油马路。能在林间小路结束旅程,想来也是极好的。但沿此路上山绝非易事,有时山路变得十分陡峭,甚至需要使用链绳把人拉上岩石。
上山时天朗气清,我们会偶尔会透过树林瞥见下面的城市;但当我们到达的山顶时,浓雾笼罩。站在基督像脚下,你甚至看不清雕像的面庞。自然地,我感到有些失望。雪琳一如既往地满怀希望,想着云雾会消散。但是并没有。
朝圣途中,人们会试图解释发生的一些事情,将其视为某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而非认为云雾不过是自然条件下微小水珠在高空的集合——即使事实本来如此。人们这样做一定是因为没有机会再去享受这个过程了。虽然有些令人失望,但这确实是这3025公里徒步的终点,今天也是里约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协定生效的日子。正如计划的一样,我们在今天抵达了这里。我们明天不会为了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的景色而再来一趟,否则不如看看照片。
我站在的云雾遮蔽的峰顶,远离人群,陷入了几分钟的沉思。想来晦暗的天气也不无好处,起码发人反思——如果基督的面庞被云雾包裹并非基督刻意发出的信息。我意识到就“宣传解奥林匹克休战协定”这一目标而言,我们所做的在某种程度是背道而驰。我的结论是: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充其量只是有限的。当我们的安全和自由正在被邪恶、可恶的恐怖主义威胁时,有关和平的讯息也许不会流行。现实可能就是如此。此外,如果休战的信使只是一个孤独的前政治家,而不是迷人的奥运参赛选手,为什么有人会听得进去?这点不错。如果我把之前徒步的四个月花在说服法拉赫这样的人,鼓励其站出来为奥林匹克休战协定发表哪怕只有30秒的演讲,难道这样不会更有效果吗?肯定是的。
此时我朝对面望去,雪琳仍在来回奔波组织人员,拍摄照片,交换联系方式,并筹办下山的交通,我开始反思此次徒步的第二个目的: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对此我的结论更加乐观一些——250,000英镑可以对世界各地的儿童的生活产生切实的积极影响。但我们能通过一次更加具有象征意义的短距离徒步筹集到这么多款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是雪琳组织的话。所以我115天、32025公里的徒步是绝对必要的吗?也许并非如此。不过如果云雾开始消散,我或许又改主意了,谁知道呢。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