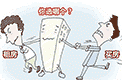(我一直待在酒店的早餐区,因为只有这个地方的WIFI强一点,能支撑我打开博客。)
新伊瓜苏炎热而潮湿,我疲惫不堪,只想赶紧上床去睡觉,因为明天是个大日子:经过最后25英里的跋涉,我就将到达里约市中心。雪琳在我旁边忙个不停,拼命给潜在的捐赠人发送微信消息。我们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集的善款快达到25万英镑了,雪琳决心要进行最后的冲刺,冲破25万英镑大关。
在里约找到住处对雪琳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2星级、3星级酒店的价格在4月份还是每晚30英镑,现在已经逼近每晚300英镑了,这还得取决于他们有没有空房。这就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供需现实。
徒步的时候,每一天的行程都是确定的——起点在哪儿,终点在哪儿,中途在哪儿汇合、一起去车上吃午饭。我们已经走过了许多个这样的日子,但过去几天的生活却与之前大相径庭,因为我们要开始准备周五在拉赫公园的终点庆祝仪式了。周五当天会有一些会面,比如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会面、参观市政厅等,其中许多具体细节都需要事前商议好。后援车也得在周五送回奇瑞在圣保罗的分公司,这样换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有4大袋行李要搬。次日,我们要飞到贝洛奥里藏特,这里是英国队的训练中心,也是我儿子亚历克斯的家,我们会在那儿待上几天。
我们和英国领事馆的马塞拉·特维拉一直保持联系,她为终点庆祝仪式和媒体采访的筹备工作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我们的行程一下子变得不确定了。每个钟头都会有新问题出现,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措施。这种不确定性令我感到不安、忧虑。不管是干什么,我都讨厌自己迟到。当别人说“你可以在几点到哪个地方见哪个人吗?”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要是我在进城时拐错了一个弯,迟到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没关系”,但实际上这“有关系”,因为我本就应该早点到,或者准时到,而不是迟到。
关于路线的选择有很多争论。环球报的安德鲁打电话来推荐我继续走116号和101号主干道,领事馆的马塞拉也是这么想的。但雪琳对此不太确定,因为这条路线更长,要多走5公里,而且我们还有时间限制。她推荐我走R083号公路,这条路更直。到达新伊瓜苏后,我沿着铁道走了一条更直接的路线。这段路我走的很紧张,因为要经过一些不安全的街区。我可以一直低着头以不被注意,但当我需要频繁停下来用手机查找路线或者询问方向时,这就非常惹人眼球了。这不是对巴西的偏见,而是我在22个国家的徒步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进入大城市时,你得格外小心。我喜欢一直低头快走,保持前进(否则我的生命就无法前进了)。
我发觉这和长途飞行有点相似。在飞行途中你可以进入自动飞行模式,偶尔拨一下转盘即可,但当“准备降落”的通知响起时,你便得打起十万分的精神。一下子,大包小包都得放回行李舱内,座椅要调直,娱乐影音系统要关闭,耳机也必须交还。这时候你会有一种紧迫感,而不是舒适感。最后的20分钟好像有2小时那么长。不过你很快就会听到滑轮触地的声音、机身受到阻力时引擎发出的轰鸣声,这也意味着你的旅途到达了终点。我需要的不是任何阻力,而是强大的助推力,让我从新伊瓜苏到达里约。而通常情况下,雪琳就是我的助推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