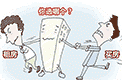尽管很享受住在Fazenda Constantinople 酒店的时光,今天却已是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晚饭后布鲁诺邀请我们去挑一张DVD观看,说真的,可供选择的英文电影并不多,我最后挑了《绿野仙踪》,结果却不由得忾然叹息。
我想,要想测试一个人有多么愤世嫉俗和多愁善感,那么观看《绿野仙踪》将是不二之选。
当桃乐茜(朱迪 · 加兰饰演)初啭歌喉,我已被深深吸引:
“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
那里是一块乐土,我曾在摇篮曲中听到过;
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
天空一片湛蓝;
即使风暴来袭,敢想的梦都能实现。”
很难相信这部电影是在1939年拍摄的,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刚刚爆发,朱迪 · 加兰也只有17岁。这是米高梅有史以来预算最多的电影之一,但它并没有让公司立刻获利,直到十年后重新上映,《绿野仙踪》才真正火了起来。
让我陷入沉思的是电影的末尾部分:为了(再次)拯救小狗托托,桃乐茜错过了和奥兹巫师一起乘坐气球回到堪萨斯的机会,她一时忧心如焚。南方的善良女巫葛琳达这时前来安慰桃乐茜,并问她在奥兹国学到了什么。桃乐茜顿了一顿,答道︰
“嗯,我……我觉得……想见到亨利叔叔和婶婶艾姆并非我内心现在唯一渴望的……另外,如果再给我一次找寻内心渴望的机会,除了自家后院,我哪都不去。因为如果在那都找不着,在别的地方就更找不到了。”
见到自己的至亲时,我大约跟小桃乐茜一样感性。但是她说的对吗?如果在自家的后院找不着内心的渴望,在别的地方就更找不到了吗?我现在坐在巴西山野丛林之中,我的一生从不曾离家如此遥远。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挑战与困难,我却意外地感觉平静,或许平静就源于这些挑战与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雪琳此时此刻和我在一起,她同样也是离家千里。
那么到底哪里才算是家呢?家是一个具体地点吗?如果这样定义的话,我的家在哪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住过许多城镇:盖茨黑德、米德尔斯堡、吉斯伯勒、威特尼、杜伦和伦敦。这些城镇对我来说都别具意义,也承载着特殊的回忆,真令我难以抉择。
我爱我现在居住的伦敦,我想念开在维多利亚街上我最喜爱的星巴克咖啡店,我想念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晨祷,我想念走过皇家骑兵阅兵场时碎石发出的“夸嚓夸嚓”的响声,我想念寇松(Curzon)电影院,我想念走在泰晤士河岸边的时光,我想念在河岸街Co-op便利店购物的时刻,我想念在考文特花园的斯坦福斯书店浏览地图系列图书,我想念天空卫视的高清足球比赛,我想念我的书,可难道这些就是我内心的渴望吗?
内心的渴望就在此时所在之地,别无他处可寻。找寻内心的渴望不在于找到一个地点,而在于发现生活的目的。而且内心的渴望需要一个人来分享。所以我来到了Cajati镇,我没有红色魔鞋,不能敲敲鞋子、念着咒语就能在一瞬间回到家乡。但我有目标、一双磨破了的乐斯菲斯徒步鞋和一个能够分享自己内心渴望的人。我并不想挑战“绿野仙踪”的哲学观,但认为自己更倾向于马文·盖伊的“脱帽安歇之处,皆是我家”的说法。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