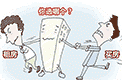(我一直待在酒店的早餐區,因為隻有這個地方的WIFI強一點,能支撐我打開博客。)
新伊瓜蘇炎熱而潮濕,我疲憊不堪,隻想趕緊上床去睡覺,因為明天是個大日子:經過最后25英裡的跋涉,我就將到達裡約市中心。雪琳在我旁邊忙個不停,拼命給潛在的捐贈人發送微信消息。我們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籌集的善款快達到25萬英鎊了,雪琳決心要進行最后的沖刺,沖破25萬英鎊大關。
在裡約找到住處對雪琳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2星級、3星級酒店的價格在4月份還是每晚30英鎊,現在已經逼近每晚300英鎊了,這還得取決於他們有沒有空房。這就是你不得不面對的供需現實。
徒步的時候,每一天的行程都是確定的——起點在哪兒,終點在哪兒,中途在哪兒匯合、一起去車上吃午飯。我們已經走過了許多個這樣的日子,但過去幾天的生活卻與之前大相徑庭,因為我們要開始准備周五在拉赫公園的終點慶祝儀式了。周五當天會有一些會面,比如與國際奧委會主席會面、參觀市政廳等,其中許多具體細節都需要事前商議好。后援車也得在周五送回奇瑞在聖保羅的分公司,這樣換酒店的時候,我們就有4大袋行李要搬。次日,我們要飛到貝洛奧裡藏特,這裡是英國隊的訓練中心,也是我兒子亞歷克斯的家,我們會在那兒待上幾天。
我們和英國領事館的馬塞拉·特維拉一直保持聯系,她為終點慶祝儀式和媒體採訪的籌備工作中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我們的行程一下子變得不確定了。每個鐘頭都會有新問題出現,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解決措施。這種不確定性令我感到不安、憂慮。不管是干什麼,我都討厭自己遲到。當別人說“你可以在幾點到哪個地方見哪個人嗎?”的時候,我就開始擔心——要是我在進城時拐錯了一個彎,遲到了怎麼辦?他們會說“沒關系”,但實際上這“有關系”,因為我本就應該早點到,或者准時到,而不是遲到。
關於路線的選擇有很多爭論。環球報的安德魯打電話來推薦我繼續走116號和101號主干道,領事館的馬塞拉也是這麼想的。但雪琳對此不太確定,因為這條路線更長,要多走5公裡,而且我們還有時間限制。她推薦我走R083號公路,這條路更直。到達新伊瓜蘇后,我沿著鐵道走了一條更直接的路線。這段路我走的很緊張,因為要經過一些不安全的街區。我可以一直低著頭以不被注意,但當我需要頻繁停下來用手機查找路線或者詢問方向時,這就非常惹人眼球了。這不是對巴西的偏見,而是我在22個國家的徒步中所總結出來的經驗——進入大城市時,你得格外小心。我喜歡一直低頭快走,保持前進(否則我的生命就無法前進了)。
我發覺這和長途飛行有點相似。在飛行途中你可以進入自動飛行模式,偶爾撥一下轉盤即可,但當“准備降落”的通知響起時,你便得打起十萬分的精神。一下子,大包小包都得放回行李艙內,座椅要調直,娛樂影音系統要關閉,耳機也必須交還。這時候你會有一種緊迫感,而不是舒適感。最后的20分鐘好像有2小時那麼長。不過你很快就會聽到滑輪觸地的聲音、機身受到阻力時引擎發出的轟鳴聲,這也意味著你的旅途到達了終點。我需要的不是任何阻力,而是強大的助推力,讓我從新伊瓜蘇到達裡約。而通常情況下,雪琳就是我的助推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