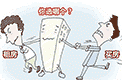盡管很享受住在Fazenda Constantinople 酒店的時光,今天卻已是住在這裡的最后一晚。晚飯后布魯諾邀請我們去挑一張DVD觀看,說真的,可供選擇的英文電影並不多,我最后挑了《綠野仙蹤》,結果卻不由得愾然嘆息。
我想,要想測試一個人有多麼憤世嫉俗和多愁善感,那麼觀看《綠野仙蹤》將是不二之選。
當桃樂茜(朱迪 · 加蘭飾演)初囀歌喉,我已被深深吸引:
“彩虹之上的某個地方,
那裡是一塊樂土,我曾在搖籃曲中聽到過﹔
彩虹之上的某個地方,
天空一片湛藍﹔
即使風暴來襲,敢想的夢都能實現。”
很難相信這部電影是在1939年拍攝的,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剛剛爆發,朱迪 · 加蘭也隻有17歲。這是米高梅有史以來預算最多的電影之一,但它並沒有讓公司立刻獲利,直到十年后重新上映,《綠野仙蹤》才真正火了起來。
讓我陷入沉思的是電影的末尾部分:為了(再次)拯救小狗托托,桃樂茜錯過了和奧茲巫師一起乘坐氣球回到堪薩斯的機會,她一時憂心如焚。南方的善良女巫葛琳達這時前來安慰桃樂茜,並問她在奧茲國學到了什麼。桃樂茜頓了一頓,答道︰
“嗯,我……我覺得……想見到亨利叔叔和嬸嬸艾姆並非我內心現在唯一渴望的……另外,如果再給我一次找尋內心渴望的機會,除了自家后院,我哪都不去。因為如果在那都找不著,在別的地方就更找不到了。”
見到自己的至親時,我大約跟小桃樂茜一樣感性。但是她說的對嗎?如果在自家的后院找不著內心的渴望,在別的地方就更找不到了嗎?我現在坐在巴西山野叢林之中,我的一生從不曾離家如此遙遠。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挑戰與困難,我卻意外地感覺平靜,或許平靜就源於這些挑戰與困難。為什麼呢?因為雪琳此時此刻和我在一起,她同樣也是離家千裡。
那麼到底哪裡才算是家呢?家是一個具體地點嗎?如果這樣定義的話,我的家在哪真是一個問題,因為我住過許多城鎮:蓋茨黑德、米德爾斯堡、吉斯伯勒、威特尼、杜倫和倫敦。這些城鎮對我來說都別具意義,也承載著特殊的回憶,真令我難以抉擇。
我愛我現在居住的倫敦,我想念開在維多利亞街上我最喜愛的星巴克咖啡店,我想念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晨禱,我想念走過皇家騎兵閱兵場時碎石發出的“夸嚓夸嚓”的響聲,我想念寇鬆(Curzon)電影院,我想念走在泰晤士河岸邊的時光,我想念在河岸街Co-op便利店購物的時刻,我想念在考文特花園的斯坦福斯書店瀏覽地圖系列圖書,我想念天空衛視的高清足球比賽,我想念我的書,可難道這些就是我內心的渴望嗎?
內心的渴望就在此時所在之地,別無他處可尋。找尋內心的渴望不在於找到一個地點,而在於發現生活的目的。而且內心的渴望需要一個人來分享。所以我來到了Cajati鎮,我沒有紅色魔鞋,不能敲敲鞋子、念著咒語就能在一瞬間回到家鄉。但我有目標、一雙磨破了的樂斯菲斯徒步鞋和一個能夠分享自己內心渴望的人。我並不想挑戰“綠野仙蹤”的哲學觀,但認為自己更傾向於馬文·蓋伊的“脫帽安歇之處,皆是我家”的說法。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