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茨勛爵徒步日志:Day34 (5月9日):樂天派
“悲觀者在機遇中看見困難,樂觀者在困難中看見機遇。”
——溫斯頓·丘吉爾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我的大兒子馬修的29歲生日!馬修住在德克薩斯州,所以我通過WhatsApp手機App祝他生日快樂。馬修有很多令我喜愛的品質,其中一個就是他的樂觀。
10歲時,他想要追隨貝克·漢姆的腳步為曼聯效力,甚至對此感到痴迷。但那時他未能加入校足球隊,因此我被派去跟他進行“爐邊談話”,試圖溫和地幫助他開拓視野,找到更實際的目標。
我說,“馬修,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你沒能加入曼聯,你會干些什麼?”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當時的表情,好像難以相信我竟問了這麼一個問題。平復后,他說,“那我可能會為切爾西效力。”說完便帶著足球去花園練習了。
馬修最后沒有加入曼聯或是切爾西。事實上,他實現了更高的成就——他的籃球水平無論是在英格蘭還是美國都屬一流﹔他在德克薩斯州貝爾頓市有一份很棒的工作﹔他家庭美滿,有嬌妻愛子相伴。我為他感到自豪。他的這些成就和他的生日也引發了徒步中的我對樂觀主義的思考。
本質上我是個樂觀主義者——18歲就加入保守黨、支持紐卡斯爾聯隊的人怎會不樂觀呢?這種樂觀精神可能根植於我的基因中,流淌在我的B型陽性血中吧。樂觀的態度在徒步中對我幫助很大,我更願去相信,明天會是天氣晴朗的一天,可以洗上熱水澡而不是冷水澡﹔明天會途經這樣一家加油站,那兒便利商店裡的冰箱裡裝滿了冰鎮的健怡可樂﹔明天的落腳點有wifi,還有手機信號……
想起積極樂觀時,我總是先想到雪琳,進而想到中國人。像美國人一樣,中國人有著積極向上的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杯子總是半滿的,而不是半空的,這也是他們做生意做得好的原因。他們相信成功就在不遠處。輿觀調查網為英國《獨立報》做的一項民調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卻也充分証明了中國人的這一民族特性。
調查於2015年11月至12月期間展開,其中一個問題是,“你認為世界在變好嗎?是/否”(暫停一下,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據調查顯示,在英國隻有4%的受訪者認為世界變得越來越好,法國還要少,隻有3%,德國也是4%。在所有歐洲國家中,瑞典是最樂觀的,這一數值達到了可觀的10%(不過我們仍要意識到,還有90%的人認為世界沒有在變好)。在印度尼西亞,相信世界在變好的人數百分比達到了驚人的23%,但和中國這一世界上最樂觀的國家比起來還稍顯遜色,因為中國有41%的受訪者認為世界在變得越來越好,這一數值是英國的十倍。
這重要嗎?當然,十分重要。不管你認為自己行還是不行,你有可能都是對的,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影響著我們的實際行為。如果你相信世界即將墜入一個無底的黑色深淵,那你很可能會變得死氣沉沉:不會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不會去努力創業,不會去創造新發明。“為什麼要白費力氣,反正結果一樣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影響著經濟發展,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經濟年增長2%就會被西方財經評論員稱為復蘇,而中國經濟增速6%還要被他們稱作是減速了。
世上最偉大的散文之一出自一位美國女士,海倫·凱勒之手。這篇文章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的作者從小失明、失聰,在她的老師安妮·莎莉文的幫助下,才學會了說話、閱讀、寫作。這篇散文寫於1903年,那時海倫剛學會把紙張印在槽板上寫字,板上的溝槽和索引筆可以幫助她書寫。這裡有一段節選:
曾經我隻知曉黑暗與死寂,現在我還懂得希望與歡樂。曾經我焦躁不安,不斷沖撞那道將我禁閉起的圍牆﹔現在我欣喜地意識到,自己還可以獨立思考、付諸行動,從而到達自由的天堂……一個沖破了生命禁錮,感受到自由所帶來的狂喜與榮耀的人,怎會再甘願做一個悲觀者?!我早年的經歷就是從悲到喜的一次飛躍。在我主動運用第一個單詞時,我就沖破了束縛、投入了光明:我學會了如何真正地活著、如何思考、如何滿懷希望。
我能想象這樣一幅畫面:馬修從閣樓上的舊箱子裡翻出了貝克漢姆的曼聯7號球衣,抱起足球,跑進花園開始特訓。兒子,你永遠不知道曼聯什麼時候會給你打電話請你去效力!保持樂觀,勿忘夢想!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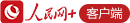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