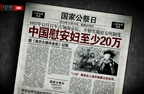1978年21歲時的合影

50歲左右時的合影
看不見的階層:14人的56年
人生到底是怎樣被決定的?英國格拉納達電視台拍攝播出了來自英國不同地區和家庭的14位孩子從7歲到56歲的人生經歷,默默追問決定人生的答案。這不僅僅是一部史無前例引人思考的紀錄片,或者說,這是一個追問普通人命運的社會學研究報告。
看到他們小,看著他們老,看他們努力奮斗,看他們徒勞掙扎。他們是他們,但他們也可能是你、是我。沒有什麼比這更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感慨萬千的了。
1964年,英國格拉納達電視台拍攝播出了40分鐘的紀錄片《7歲》,選取來自英國不同地區和家庭背景的14位7歲孩子,用紀錄片手法拍攝他們的生活、言談和想法。那些鏡頭,記錄在當時的黑白膠片上。
2012年5月,《成長》(Up)系列紀錄片的第八集《56歲》(56Up)播出,當年的那些孩子,已是天命之年,用來記錄他們人生感悟的,不再是膠片,而是最新的數碼技術。
全世界迄今為止可能都找不出第二部這樣的紀錄片了——真實,真實到駭人,直面生活的殘酷和美好。前后跨越半個多世紀,從1964年至今,影片七年一拍一播,《7歲》、《7歲又7歲》、《21歲》、《28歲》、《35歲》、《42歲》、《49歲》到《56歲》,不脫節地記錄了一代普通英國人的大半輩子。
從《7歲》到《56歲》,這部紀錄片系列劇每每播出都在歐美收獲極高的收視率。據說,符合好萊塢的成功票房標准的劇本,必須在兩個小時之內包含60個戲劇性的起承轉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成長》系列以14位你我這般普通人的原生態生活為劇本,用跨越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來完成14個不同“命運”的種種起承轉合,可謂將 “戲劇性”發揮到了極致——他們見識了出生和死亡,經歷了結婚、離婚和再婚,有背叛,有妥協,有的曾精神恍惚,有的被迫下崗,有的蠅營狗苟過活,有的幸福美滿……電視機前的你看著少年時的他們對人生充滿未知和憧憬,看著青年時的他們放蕩不羈冒傻氣,看著壯年時的他們幸福或不幸,看著中年后的他們變得百困不侵、安於自嘲。
生活是無法超越的劇本。
七歲定終生?
1964年 《7歲》初拍時帶有實驗性質,格拉納達電視台是把它當作一個時事類節目做的。他們想表現的是戰后經濟繁榮下,傳統的英國階層、特別是中下階層正在經歷大變化這一現象。大背景是,就在此前一年,英國的社會學家約翰·勾索普和大衛·洛克伍德就 “超階級理論”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討論。“超階級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財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過自身努力奮斗或其他綜合因素,從社會底層或工人身份蛻變脫離,言談舉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進入“中產”行列。
所以從一開始,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將討論的目標內容圈定在“階級”二字。傳統英國社會,窮富分化,階層分明。住的地方、吃的東西、看的報紙、上的學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階層之間差別大得很。《7歲》開拍,導演不想循規蹈矩找一些政界學界的人來說大道理,靈機一動搞“創新”,去英國的不同的地區找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成長環境的14個孩子:有的孩子就讀高級寄宿學校,屬於精英階層﹔3位女孩出身東倫敦的貧民區,兩個來自“兒童之家”、在沒有父母關護的情況下長大,另一個出自農村山區,都算社會最底層﹔另幾個是家住老工業重鎮利物浦的后代。節目試圖通過與孩子的對話,不動聲色地彰顯“階層”在他們身上烙刻的印記。
從七歲孩子的回答裡,還真就能看出點什麼來。約翰、安德魯和查爾斯讀的是肯辛頓的高級寄宿學校,問到他們的閱讀習慣時,丁點大的安德魯說他讀《金融時報》,約翰說他看《觀察家報》和《泰晤士報》。他們已會用拉丁文唱歌,並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師,要上劍橋的三一學院。而對出身東倫敦的托尼來說,將來能做個“賽馬騎手”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興奮不已了。同樣七歲,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兒童中心長大的西蒙,完全沒有約翰他們的寬闊“眼界”,更未曾規劃過自己的將來。能有機會見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經很高興了。有人問他“你怎麼看有錢人”時,他回答“沒想過”。當時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見過真正的有錢人。
拍攝《7歲》時,英國大導演邁克·艾伯特在劇組做案頭資料收集。他回憶說,盡管開播后反響很好,《7歲》的主創壓根沒想過要做續集,更沒想過有朝一日它會成為世界上歷時最長的紀錄片。直到《7歲》開播五年后的一天,格拉納達電視的老板在餐廳和他一起吃飯,突然來了靈感,建議拍個續集。大家都覺得有意思,於是就有了《7歲又7歲》。片子就由當時已在格拉納達電視台混出老資格的邁克·艾伯特執導,此后所有的《成長》系列,全都是他的導演手筆。
在艾伯特看來《7歲又7歲》並不成功。“14歲的孩子總有點混,青春期麼,問十句答一句,整部片子談不上精彩,這甚至不是一部成功的片子。”但撇開可看性不說,邁克和他的團隊就是從《7歲又7歲》和后來的《28歲》起開始意識到,要真能做到“七年一追蹤”忠實記錄這些孩子的成長,直到他們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再對比他們的生活處境,也許比單部《7歲》來得更震撼人心。
觀察這14個孩子的成長軌跡,邁克·艾伯特說,既“有趣”又“令人心寒”。有些人很早就對人生、對社會有一定的認知和遠見﹔有些則一輩子每天都忙著為當天的生計操心。相隔50年回頭看,依舊是幾個來自精英階層孩子的人生相對光鮮。他們過著優渥的生活,婚姻穩定。安德魯劍橋畢業后成為一名律師﹔約翰投身慈善業,娶了駐保加利亞大使的女兒﹔幾位出自中產家庭的女孩大多生活平淡滿足,且都嫁得不錯。他們大多保養得當,神採煥然。同是女性,來自東倫敦底層的林、蘇和杰姬則命運坎坷,其中蘇相對幸運,在學校做行政,再婚后組建的家庭生活幸福。出自底層的兩個在慈善機構長大的孩子,一個成了卡車司機,另一個是養老院工作人員。夢想要當賽馬騎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車司機,婚姻中出軌被老婆抓了正著,后來取得了妻子的原諒。
14個孩子中,有兩三個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奮斗,躋身真正中產或准精英階層。就讀公立學校的布魯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約克郡農庄的尼克,成為一名核物理學家。
而那些原本身處社會中層的孩子的命運,反映出更多不確定性。利物浦的彼得長大后成了一名教師,曾言辭激烈抨擊撒切爾的教育政策,后來改行做公務員,家庭幸福,兒女雙全都非常優秀,業余時間和氣質優雅的妻子一起搞樂隊作表演。曾與彼得同上一所學校的內爾,卻在申請牛津失利后命運一落千丈。照理他還是可以上個大學完成學業,走一條和彼得差不多的中產道路,但內爾沒有。他輟學、在建筑工地當臨時工,甚至一度流離失所,隻在最近幾年境況才有所好轉,目前是倫敦東區的一位政府咨詢公務員。
從《7歲》到《56歲》,每一集影片都以一句慧語開篇:“讓我帶一個孩子到七歲,以后隨你怎樣帶,隨他怎樣長,他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已是注定。”這和中國的老古話“三歲看七歲,七歲定終生”是一個意思。對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人來說,人生是一張測繪好的地圖。
“上帝”之眼
能堅持50年拍這樣一部紀錄片的,可不是什麼一般人。邁克·艾伯特是聞名好萊塢的大片導演。他執導過《礦工的女兒》,其中的女主角希希·斯帕塞憑此片勇奪奧斯卡﹔他執導的 《迷霧中的大猩猩》曾獲得五項奧斯卡提名﹔他還導演過007系列電影《黑日危機》、《納尼亞傳奇3》。雖然艾伯特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但他的事業發達和好萊塢脫不開干系,為了工作方便,他本人常年在美國居住。
與率領幾千人大軍回英國拍007的那種規格相比,《成長》系列對他來說連“小成本”制作都算不上,但艾伯特卻將這一系列紀錄片看作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他的“宣言”。盡管他本人正是出自富有家庭,22歲劍橋畢業后順利被招入電視台工作,他一直覺得自己多少是借了“好出身”的光,且對英國社會“階層決定命運”的不公非常看不慣。雖然他手裡總有片子要拍,但每隔七年,哪怕再忙,他都會放下手頭的工作,排出六個月的檔期來拍這部《成長》系列。
時間檔期倒不算什麼。最大的挑戰是,怎麼聚齊當年的這14個人。“他們在還不懂事、沒權利說‘不’的時候就拍了第一部,但隨著他們的長大,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將他們的生活展現在公眾視線內”,艾伯特說,說到底,他和這14個人之間沒有任何合約合同,全看他們是否自願。拍了近50年,當年的14個孩子,除了查理《7歲》之后再沒出過鏡,其余的13名孩子都斷斷續續參與至《56歲》,他們有的曾因某期節目中言辭激烈而遭遇很大輿論壓力,有的遭受精神疾病,有的經歷婚外情,這些人都沒有避諱對艾伯特敞開大門,讓他“記錄”並公開他們的生活,對於導演來說,這可是了不起的戰績。他到底用了什麼方法?“威逼利誘”,他笑著說:“金錢報酬是肯定的,盡管數目很少。我總會盡量想辦法找點錢,每一集都給得比上一集更多一點。早先我還比較多用情感攻勢,我會對他們說,你們都已經做了那麼多集,現在退出豈不可惜?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的生活能這樣被完整地記錄呈現?我還會用我自己來現身說法,無論我生活中發生了什麼,每七年的這個時候,我一定會投身做這件事情,因為我認為它很重要。”
珍惜也好、認同也好,或是想要借這個平台達到個人的宣傳目的也好,就算這些人同意參與攝制,要集齊他們也不容易。拍《28歲》時,攝制組整整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在蘇格蘭的某個地方找到精神恍惚的內爾。到了《49歲》時,又是一通好找才發現他早就離開了蘇格蘭到了倫敦的一個區裡尋活計﹔拍 《56歲》時,因為其中的保羅已經移民去了澳大利亞,為了拍他整個組飛到了澳大利亞。
一直跟蹤看這部片子的人們覺得艾伯特通過它賦予了觀眾 “上帝之眼”,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有人可以如此詳細地近距離觀察到那麼多個陌生人的大半輩子。但扮演“上帝之眼”的那個攝像機鏡頭,以及鏡頭后的“腦子”即艾伯特這位導演,真能做到隻客觀記錄、不主觀判斷嗎?“我盡最大的努力做到客觀,有時候我知道問題很尖銳,但我不得不問。要是我不問,觀眾會有疑問。”艾伯特說,“但做到純粹客觀真的很難,有時候最終在屏幕上呈現出的那些鏡頭,多少是在表達我個人的觀點、判斷和解讀。我后來盡可能爭取做到平衡、抽離、客觀,但我還是犯過錯誤。比如拍《28歲》時,尼克的太太對我意見很大,認為最后的成片中我把她拍成了一個糟糕的女人。她拒絕再合作,也不讓尼克出鏡。當然,不久之后他們的婚姻就走到了盡頭,他們之間的確有很大的問題,但和我以及這部片子都沒太大關系。”
托尼的例子更令艾伯特 “覺醒”,原來他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中,試圖以上帝的姿態去“預測”這個孩子未來的命運:“在拍《21歲》時我幾乎認定這孩子將來遲早會進監獄,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很多鏡頭都給到倫敦的那些犯罪率的高發地點。但事實証明我錯了,教訓很深刻,我感到尷尬。自此我知道,我越少‘引導、判斷’越好。每一集開拍之前,我盡量都做到將此前發生的清零,相當於一張白紙,從頭開始。”
盡力客觀並不代表艾伯特就不講人情,某位參與者的孩子身上出了件大事,他特意剪去了那一部分沒有播出。因為這部片子,這些當年的孩子和導演艾伯特已成為某種程度上的“一家人”。
后來生活一直不太如意的內爾說,要不是這部片子,他根本從未意識到自己還曾是那樣的一個陽光少年!
片子會結束,生活會繼續
任何紀錄片終究會完,哪怕故事本身未竟。再一個七年,生老病死可能成為下一部《63歲》的主題。這14位孩子都還算幸運,至今除了一位叫林的在35歲和42歲時得了一種怪病外,其余人都健康無憂。布魯斯說,他有意在《56歲》之后就不再參與錄制這個節目,因為“到了56歲我們大家的這輩子基本定性,再往下錄,多半就是誰還活著、誰先走一步的問題了”。
但艾伯特會堅持把這部用半輩子時間“腌制”的紀錄片進行到底,拍到客觀條件不允許它拍下去為止。“人們問我,下一部你准備怎麼拍,如果這些人中有人死去、有人得病了,你還怎麼拍?我現在說不出,也許到時候我就知道怎麼辦了。”艾伯特開玩笑說,“希望我可以不用面對這難題,希望我是最先走的那個人。”他本人今年已經73歲,“算起來要真有 《84歲》的話,我都101歲了!要能這樣畫上句號,那將是一曲多麼美妙的天鵝挽歌!”
作為一名電視電影的導演,邁克·艾伯特此生最得意的作品並非奧斯卡提名電影或票房大片。對他而言,正是這《成長》系列體現了他的情懷,是他這輩子最驕傲的作品:“迄今為止的電視娛樂時代,沒有一部紀錄片有這個耐心、跨度和時間,來為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唱響贊歌。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以紀錄片形式做過的時間跨度最長的社會學研究。僅就這一點,它將被世人記住,它體現了紀錄片的‘意義’所在。”
還不止如此,最打動人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進,這部紀錄片每播放一集,都似乎是在提醒人們:一切都會過去﹔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人都在用堅毅和幽默來直面並不順遂的人生。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